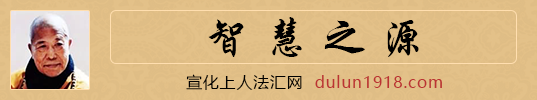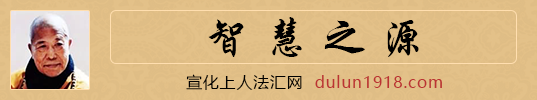◎比丘尼恒持二○一四年三月十四日讲于万佛圣城大殿
我记得刚开始学讲法是在佛教讲堂,地点位于三藩市的唐人街,距离我们现在的金山寺不远。那时候师父要我们赶快学会讲法,所以他就分出时间让我们来学讲,就像今天晚上一样,上人会留三十分钟给一个指定的人来练习;那时候我们大部份的人都是这样学的。
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经验,所以开始的时候很辛苦,几乎每一个上去讲的人,开头都是用很小的声音对大家说:「阿弥陀佛,今天轮到我,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,我也没有准备。」后来我就学会了,我跟自己说:「如果你要讲法,你必须要有法可以讲。」以后,我每次就会选一个法来说。譬如,我喜欢的七菩提分,这个对修行很有帮助,或者八正道,或者四圣谛,或者其他的。如果你懂佛法,准备一个自己的目录,然后从里面选一个题目来讲,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当你在讲的时候,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,而且因为有准备,就不用每次都要跟人家赔不是。八万四千法门,好多好多,门门都是佛法,不是吗?所以一定有东西可以讲的。
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,大学的时候也没拿过中文课,所以中文的四声念得很糟糕。每次要讲法之前,就像今天晚上,为了要自己翻译中文,就得先把字写出来,然后查字典,把四声查好,这样才不会因为说错让自己和其他人难堪。我的中文可能说得还不是很正确,而且也不应该这么自负,所以还是请别人帮我翻译好了。可是如果他们帮我翻译,你就不知道我这个美国人是会说中文的,所以容许我对会讲中文这一个小小的自豪,忍耐一下我的四声。
今晚我就讲师父的一个偈颂:
觉者慈悲摄有情 圣贤设教化顽冥
世尊种族佛宝印 灯灯互照心传心
讲到佛教讲堂,我就想起那时的观音七,也就像我们现在要开始的观音七一样。除非你不常来,要不然你一定知道,观音七的时候是念〈普门品〉。〈普门品〉很好听,大家都喜欢,所以每次拜完以后大家都开心。诵完〈普门品〉然后呢,就念观音菩萨名号,走一走,再坐着念,接下来止静一下,就是这样子。我要说的是有关静坐这个部分,因为那段时间是一个禅七。
那个时候在佛教讲堂,我们打了一个九十八天、十四个礼拜的禅七。大概是在第三个礼拜的时候,师父买下了第一个金山寺,所以差不多有一半的人,都必须离开去装修金山寺,其他的人,包括我在内,就留在佛教讲堂继续打禅七。
去过唐人街的人都知道,一面墙壁两户人家共有,没有缝隙,所以邻居做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刚好就面对那一道墙打坐,工人在那边拆楼,我和其他三十几个留下来的人就在这边打坐。师父有先见之明,在走之前给我们开示,他说:「你们要忍耐,不要生退心,无论怎么样的情况,都不要生退心,即使有人要把你周围的房子拆下来了,也不要生退心。」结果他们离开之后,隔壁就开始拆房子。
那一次他们好像几乎要把整栋楼拆下来,我一直记得上人说的话:「不要生退心!」就坚守不退。
除了邻居拆房子整修的噪音之外,还有街上传来中国京戏的音乐。修行人有很多种,这么多年来我听到各式的抱怨,譬如:「太吵了,我受不了,我没办法打坐。那些翻纸、衣服摩擦、打嗝、换姿势的声音,让我实在无法打坐。我要有自己的空间,我要有自己的厕所,他用他的,我用我的,不然他去厕所会干扰到我!」诸如此类的。
其实,师父的训练不是那样子的,至少我自己在佛教讲堂的经验是──越吵越好。所以,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心里找一处安静的地方,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到得了;既没有噪音,也没有干扰,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,都没有人来打扰。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,那么不管在哪里都不会有问题,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到那里打坐,随时入我们自己的定。
打完九十八天的禅七之后,我就到金山寺去了。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到那边,而且又可以听师父讲法。可是谁猜得到,到那儿第一天师父就把我叫到旁边,跟我说:「果修,妳晚上还是要回去佛教讲堂。」因为有三尊佛像在那边,没有人上香不行,所以我得每天搭巴士回去上香。整个禅七期间我都没有机会听上人讲法,现在当然不可能放过。那时候金山寺还在整修,所以师父没有正式讲经,他就讲很多祖师传,当然没有人愿意错过听故事的机会。于是我每天听完师父开示,大概是九点半,然后走路到公车站搭车到佛教讲堂,沿路要转二趟车,从十五街转到三街,然后转到都板街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每天都是这样子。
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定力上下功夫,所以就开始每天持一百零八遍的〈大悲咒〉。问题是,那时候新的金山寺有很多事情要做,因为整修的关系,有人给我们很多用过的木材,虽然不用钱,但是有不少的钉子在木头里,得先拔出来才能用;再加上扫地、扫木屑,整天都很忙。有时候我忘记持〈大悲咒〉,所以晚上搭公车转车的时候,在车上就可以念我的〈大悲咒〉。如果到佛教讲堂都还没有念完的话,我就一定念完才去睡觉。
结果搭车回到佛教讲堂,还没爬到四楼,电话铃就响了。不用问都知道是谁,因为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。师父晓得我知道是他打的,可是我就是这么固执,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弟子,很不孝顺,不听话。我明明知道是师父打电话来看我是不是安全到家,可是如果〈大悲咒〉还没念完,我就不接电话。有时候还差五十遍,也不管,我就在那儿念念念,等我的〈大悲咒〉念完了才接。那个电话响五十次、一百次都可以,好像在比赛谁可以坚持久一点。念完了我赶快去接电话,师父就说:「果修!」我说:「师父!」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,就开始交谈,谁也没提起那个响了一百声的电话。
你们这些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,还有要出家的居士,不要学我的样子,我是非常固执的弟子,不孝顺,也不听话,不要像我这样子,你们要好好听话。
星期六、星期天我必须留在佛教讲堂,因为它被旧金山的「观光指南」列为一个景点,是个对大众开放的地方,可能现在还是。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道观,是三藩市道教最老的道观,所以就被用来当广告给人家参观。一般人进来就是要看道教的塑像,那时我们放了一尊白色的佛像在那些塑像的前面,因为这个原因,我们不能关门,也不能锁门,就只可以有人来了,我告诉他们:「对不起,我们没有开,今天没有法会。」
有一个星期天,来了一个奇怪的白人,一个大概五十多岁的美国人。我们是在四楼,那时我已经把门关起来了,他来敲门,我一开门看到他,觉得不太对劲,就对他说:「对不起,我们没有开。」他也没有说什么,转过身就下去了。我在里边,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不安的预感,于是就走到阳台,阳台也有一个楼梯,是火灾的逃生梯。我往下一看,这个人正爬著逃生梯要到上面来。我还是一样跟他说:「我们没开。」他也没说什么,就下去了;然后几分钟以后,他又爬了四层楼梯来到门口。
就这样来来回回僵持了一段时间,后来我就害怕了,害怕就打电话给师父。那时候打电话给师父,师父不会自己接的,金山寺的男众会接电话。但是那天很幸运,师父接了我的电话,我说:「师父有一个奇怪的人在这里,怎么办?」我把情形说给他听,他说:「不要紧,不要紧,我叫果法来救妳。」果法就是 Bob Olson,我要把这个故事献给 Bob Olson。几年前他离开我们,他是很壮的一个人,曾经卖过毒品,见过场面,知道的事情也很多。
在等果法来的同时,这个人继续爬上来一、两次,我都叫他离开,他还是一直要从逃生梯上来。后来那个人就不见了,我就在阳台等果法;看到他来,我就跟他打个手势,说:「没事了,那个人已经走了。」所以他也就不用上来。
有些人听到我说 Bob曾经贩卖毒品,好像很震惊的样子。你们不知道,到师父这里的什么样的人都有,我们可以从这个极端,变到另一个极端,也是一群放弃一切而来追随师父的美国人。认识师父之后,Bob 改变很多。师父给他很多帮助,付学费让他去学木工、水电工等等,然后他就一直帮忙照顾万佛城,直到他往生。所以我这个故事是纪念 Bob,为他说的。
好了,现在讲讲万佛城。讲到万佛城,记得那个时候是打观音七,就像现在,天气很好的。因为景仰师父,所以很多人来。绕佛的时候,师父就站在那边看我们,有些人走到师父前面就停下来给师父叩头、合掌,对师父一直拜拜拜,后面的人就都得停下来等。一个又一个的,直到师父受不了,就骂他们:「你们在做什么?你念观音菩萨就念观音菩萨,你看我、给我叩头、给我合掌作什么?」很不高兴,然后他又说:「这个星期,无论是谁,没有好好念观音菩萨,还是一直看我、对着我合掌,我就知道你不专心念观音菩萨,一点定力都没有!」大家都吓得不得了。
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做,就是〈普门品〉唸完我们会到外边绕,我们会去女校、男校,或者如来寺,就是在外面边走边念观音菩萨名号,差不多念一个钟头。
我还是那个固执的个性,一九七○年,已经到万佛城了,我还是那个样子。既然师父这样说,我心里就决定:「好!这个礼拜,我要做得最好,无论如何都不要看师父!」所以在绕的时候,我就照着戒律里头说的,眼睛只看前面地上的小圈圈,就只看那里,不看别的地方。但是奇怪,虽然那样做,我还是看到师父,因为眼睛的余光会让我知道师父在那里。
那一天我们在女校那边走,我知道师父要来了,他朝着我们一直走过来,我就提醒自己,绝对不要看师父。你猜怎么样,他直接走到我前面,然后把他的脚就踏在我眼睛看的那个小圈圈里,一句话也没说,我也不敢说一句话。师父把我看穿了,他完全知道我在做什么!
其实我不是完全不听话的弟子,给你们讲了四个我不听话故事,现在要修正一下,我也是听话的弟子。那么现在就讲一讲「听话」,因为观音菩萨代表的就是「听」。
我在一九六八年遇见师父,好几个人也都是在那前后来的。当时,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,如果你真的认识师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话,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。我们不可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,让我们这样普通的美国人能有这样的机会亲近他。当然也有不认识师父的,他们待几天就走了,因为没有被打动。
接近师父是一个机会,而第二个机会是可以认识师父,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。我跟随师父,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五年师父圆寂,总共二十七年。不过那些年里,我并不是常常在他身边的。
刚开始我们在佛教讲堂,之后就到第一个金山寺,然后再到万佛圣城。有的人说我们这里(万佛圣城)是一九七六年开始,其实不是,应该是一九七四。七四年,我们女众开始来万佛城整理收拾这个地方,你们认为现在清理不容易,那时候更不要说,我们天天就是收拾整理这些屋子。我七五年来,住在万佛城十年,虽然师父不是天天在这里,可是在的时候也不少,所以可以常常听师父讲法,真的很好。
八五年师父就问我,也不是问,是叫我,就是叫我去加拿大的金佛寺;我马上就答应了。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,我不要你们听了前面的四个故事,就觉得我从来都不听师父的话;我是听话的。
我要去吗?不要去!离开师父,离开他的法,离开天天可以听师父讲法的地方?我不想去,真的不想!!师父那时在讲《华严经》,他讲的佛法是那么微妙,又在妙语堂给我们上课;除此之外,我还参与录音以及帮上人翻译的工作。但是当他问我的时候,我马上就答应了。
虽然我的个性这么强,但是我听话,师父知道如果他叫我去,我一定会去,所以师父就是用我打头阵。一般来说,男众会先去新的道场,就是做苦功,把道场整理好了之后,师父会叫他们回来,然后再叫女众去,很多次都是我打头阵。今天要来之前,我看了一下我的护照,一直到师父走,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叫我去的,我从来毫不犹豫,都照做。
只有一次,我犹豫了一下。那个时候师父叫我回来万佛城,因为他要把所有参与佛经翻译的尼众搬到柏林根去,到那边翻译经典。我也是翻译的成员之一,可是他没有叫我去,他要我回万佛城。做什么呢?他要我管理法大、僧伽居士训练班和签证工作,在电话里他说:「还有顺便带沙弥尼。」所以我要回来做这四个工作。我真的不想回来,因为我知道师父会在柏林根,而我却得留在万佛城管理法大、僧伽居士训练班、签证和沙弥尼!但是终究我还是听话,照做了。所以今天我还在这里,我想部分原因跟听话是很有关系的。因为不听话的,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,对不对?
现在讲偈颂,第一句是:「觉者慈悲摄有情」
我们这个星期念观音菩萨,所以我选这个偈颂,因为可以说就是指观音菩萨,他用慈悲心摄受我们。师父、佛菩萨用两种不同方法摄受众生,一个是摄受,另一个是折服。虽然两个都很有效,但还是要看教化的对象而定。
这一句讲摄受。摄受有摄受的方法,另一个是折伏的方法。折伏法,令我们正视自己的烦恼、自己的缺点,然后改过。如果我们还不能接受,那就先用摄受,好比说:「你是好孩子,你还好,没有什么大问题。」先令我们接近而不害怕,不害怕之后就可以开始用折伏法,教我们有什么要纠正,有什么习气毛病要改。跟着师父就是这样,他会用折伏的方法,但是如果有的人不能忍受,他就用慈悲来摄受。天天都是这样,他注意我们每一个人,从来不会失去任何一个教化我们的机会。
第二句就说:「圣贤设教化顽冥」。顽冥,就是不太聪明的人,也可以说是愚痴的人。师父来到这里,天天就是带着我们这几个很平常的美国人,从不离开我们。你看看师父这一生,他做什么?他没有到处去,或是住在不同的地方,天天就是跟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在一起。为什么他不到处去呢?如果你知道我们以前的样子和后来的转变,有多少个出家做了出家人,甚至有多少个到现在依然继续亲近道场,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想想看,师父这么一个伟大的人,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心血那样做?
第三句就说:「世尊种族佛宝印」。在历史的记录,有这么一个释迦牟尼佛,他来到我们的世界,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凡夫可以成佛。他示现给我们看,他也是个平常人,然后在这个世界成佛。他要让我们知道,虽然世界这样杂染,我们还是可以觉醒开悟,就给我们这么一个模范。我认为师父来这个世界,也差不多是同样一个原因。表面上看来,师父好像是一个普通人;可是,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,很多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
孟子说:「仁义礼智根于心,其生色也,睟然见于面,盎于背,施于四体,四体不言而喻。」意思就是,一个有德行的人,你根本不用说话,甚至不用见他的面,光从他擦身而过的背影,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德行。师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
他来到这个世界做一个平常人,但很有德行,一直都是这样。当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很难具体说我们看到什么,很难;他走了以后,更难。所以我们这些和师父相处过的人,应该把我们看到的说给大家听,和大家分享。我想世上像他一样的人,所剩不多了,世界也变得更为不安稳。师父带来的那一种特殊的光,在他离开的时候也同时熄灭了;但是,他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。不管是直接跟过师父,或是间接读过师父的开示、听过师父的录音,师父依然活生生的在我们的心里,所以我们应该把师父所教的和大家分享。最后一句就说:「灯灯互照心传心」。这一句就讲到嫉妒心,要防备我们的嫉妒心。师父常常用「灯灯互照」做比喻,说一个灯的光线,跟另外一个灯的光线,是不会互相吵架的,也不会说我要抢你的光,或者我不给你抢我的光;它们就是合光。所以大家一起共住修行,应该要和合;然而我们最大的问题,就是彼此之间的嫉妒。
我以前大概说过我是个阿修罗,师父也说:「果修,你是阿修罗;但是不要紧,我也是阿修罗。」他是不是阿修罗我不知道,那时他看我的手掌,然后就这样说。师父也让我看他的手掌,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他是阿修罗。我猜,他这样讲是在安慰我。
你们也知道,女的阿修罗是嫉妒的不得了;我的嫉妒心是很重的,虽然我不喜欢承认。那时候我自己并没有看到,所以师父用折服法来让我看到这个缺点。的确,我是常常在和别人争。
师父告诉我,我们在旧金山国际译经学院的时候,其他的翻译人员曾跟他说,当他们不在座位时,我会跑去他们的桌子,算他们翻译的页数,然后一定要翻译得比他们多。我不记得有那样做,但是师父就是用折服法来让我明白自己的嫉妒心,嫉妒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题。祝各位晚安!